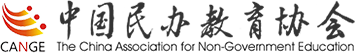目 录
一、是否可以自由约定合同解除条件?
(一)一中院:可以自由约定
(二)二中院:可以?不可以?
二、是否适用经济补偿金或赔偿金的规定?
(一)一中院:虽然违法解除但无约定不适用赔偿金规定
(二)二中院:即便是到期终止但不续签仍要支付补偿金
三、结语
1 是否可以自由约定合同解除条件?
《劳动合同法》对于合同双方尤其是用人单位有权解除劳动合同的情形有明确规定,用人单位违反规定解除劳动合同的,将承担相应的赔偿金。那么,如前述,在外国人劳动合同是否严格适用《劳动合同法》尚存解释空间的情形下,用人单位可否与外国人在《劳动合同法》规定情形之外,自由约定一些合同解除条件呢?
根据前述上海高院的观点,除“最低工资、工作时间、休息休假、劳动安全卫生、社会保险”等基本权利义务外,双方可以就其他权利义务自由约定。但在司法实践中,不同法院观点有所差异。限于篇幅,本文仅分析上海地区法院的判例。
(一)一中院:可以自由约定
在上海一中院终审的“(2020)沪01民终847号”一案中,用人单位与外籍劳动者的《劳动合同》中约定“合同终止日由董事会通过决议后,此一合同即终止之”。后用人单位通过董事会决议解除与外籍劳动者的合同,劳动者提起仲裁要求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的赔偿金以及其他请求,但未被仲裁委支持。
劳动者遂向徐汇区法院起诉,徐汇法院认为:
庄彬甫系外籍人士,根据规定,外国人在中国就业,适用最低工资、工作时间、休息休假、劳动安全卫生、社会保险等方面的劳动标准,此外,双方有其他劳动权利义务约定的,可按照约定履行。庄彬甫与新茂公司签订劳动合同约定了合同的终止条款,该约定应属有效。新茂公司据此与庄彬甫终止劳动合同有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
一审判决后劳动者不服上诉至上海市一中院,一中院审理后认定:
关于庄彬甫主张新茂公司支付违法终止劳动合同赔偿金的上诉请求,因庄彬甫系外籍人士,原审法院对其劳动法项下的权利义务的认定符合法律规定。因双方在涉及劳动合同解除的约定明确,且无涉及解除双方劳动合同需支付赔偿金的意思表示,故庄彬甫主张终止劳动合同赔偿金无法律依据,该上诉请求本院不予支持。
可见,一中院对于双方是否可以自由约定合同解除事项是持开放态度的。
(二)二中院:可以?不可以?
在二中院终审的“(2015)沪二中民三(民)终字第355号”案件中,用人单位与外籍劳动者的《劳动合同》中约定:“在合同期限内,渡边良平所在项目终止或解除,劳动合同也随之终止或解除,但需提前三十天书面通知。”
合同履行期间,用人单位赛科斯公司以原项目结束为由与外籍员工渡边良平协商调岗但未达成一致意见,赛科斯公司遂告知解除劳动合同。劳动者认为赛科斯公司违法解除劳动合同,遂申请仲裁要求支付赔偿金,仲裁委未支持其请求,劳动者又起诉至原闸北区法院。
一审法院审理认为:
上海市劳动局《关于贯彻<外国人在中国就业管理规定>的若干意见》中明确,用人单位与获准聘雇的外国人之间有关聘雇期限、岗位、报酬、保险、工作时间、解除聘雇关系条件、违约责任等双方的权利义务,通过劳动合同约定。本案双方当事人所订立的劳动合同中仅约定了合同终止、解除的条件及提前通知期的天数,并未对终止、解除劳动合同的赔偿金有过相关约定。因此,渡边良平要求赛科斯公司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126,684元的诉讼请求依据不足,不予支持。
劳动者不服一审判决又上诉至上海市二中院,二中院经审理后认为:
《外国人在中国就业管理规定》对外国人在中国就业的相关权利义务作出了规定,也对部分的劳动权利义务,明确双方可按双方劳动合同或其他协议予以确定。本案中,渡边良平、赛科斯公司签订的劳动合同对双方终止、解除劳动合同的权利义务仅作了“在合同期限内,渡边良平所在项目终止或解除,劳动合同也随之终止或解除,但需提前三十天书面通知”的规定,并未对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的情形作过相关约定,故渡边良平要求赛科斯公司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的主张缺乏依据,本院难以支持。
上述案例表明,二中院也尊重双方关于劳动合同解除的约定。
但是二中院另一个案例,态度又完全相反。在“(2017)沪02民终1039号”案件中,外籍员工姝芬与用人单位的劳动合同中约定:“若公司欲解除本劳动合同,应提前壹个月书面通知雇员。”用人单位在合同履行期间提前三个月,于2016年6月30日向劳动者发送通知称:根据你与公司签订的《劳动合同》第3.1条,终止和你的劳动合同。你与公司雇佣关系将于9月30日终止……。
劳动者以违法解约为由申请劳动仲裁,要求恢复劳动关系,但未被仲裁委支持,遂又向黄埔区法院提起诉讼。一审法院经审理后认为:
瑞贸通公司与姝芬建立劳动关系并签订劳动合同,瑞贸通公司若变更、解除或终止劳动合同的,应当依照劳动法律的相关规定执行。瑞贸通公司在没有任何点滴理由的情形下,任意与姝芬解除劳动合同,显然违反了法律的规定。瑞贸通公司的这一解约,当属于违法解约。姝芬要求与瑞贸通公司恢复劳动关系的请求,予以支持。
用人单位瑞茂通公司不服上诉,认为对于外籍员工,根据上海高院的规定可以优先适用合同约定解除。但上海二中院经审理后认为:
姝芬与瑞贸通公司之间依法建立了劳动关系,双方虽然在劳动合同中约定了瑞贸通公司欲解除劳动合同,应提前一个月书面通知姝芬。但该约定超出了劳动合同法规定的单位可以单方解除劳动合同的情形,也与劳动合同法保护劳动者合法权益的立法本意相违背。现瑞贸通公司在没有任何其他依据的情况下,仅凭该条约定来解除劳动合同,于法有悖。姝芬据此要求瑞贸通公司恢复劳动关系,合法有据,本院予以支持。
该案中,二中院又明确否认双方合同自由约定的解除条款,认为:“该约定超出了劳动合同法规定的单位可以单方解除劳动合同的情形”。
一中院和二中院对同一问题的不同看法,以及二中院对同一问题先后不同的态度,表明实践中司法机关甚至不同的主审法官,对涉及外国人劳动纠纷的法律适用,仍有不同理解。
2 是否适用经济补偿金或赔偿金的规定?
经济补偿金和赔偿金的支付是《劳动合同法》的一大特色,在实践中也成为保障劳动者权益的一项重要制度。那么用人单位与外国人之间,若出现根据《劳动合同法》应当支付经济补偿金和赔偿金的情形,是否要支付呢?
解除/终止合同与经济补偿金或赔偿金的问题是前后关联的,前述关于能否自由约定合同解除条件的案例中,已经体现了不同法院对是否支持外国人索要经济补偿金或赔偿金的不同态度,我们继续分析有关这个问题的两个典型案例:
(一)一中院:虽然违法解除但无约定不适用赔偿金
在上海一中院“(2018)沪01民终7108号”案件中,廖荠野为外籍员工,其于2015年7月1日与美味不用等公司签署了为期三年的《劳动合同》,2017年1月4日,美味不用等公司向廖荠野发送《解除劳动关系通知书》,告知因客观市场环境发生重大变化,为了有效应对市场竞争,公司进行战略调整,将于2017年1月12日解除与廖荠野的劳动关系。
廖荠野随后向劳动人事仲裁委申请仲裁,要求美味不用等公司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以及年终奖等其他请求,仲裁委经审理裁定美味不用等公司应当支付廖荠野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
美味不用等公司遂起诉至浦东新区人民法院,要求判决不予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及其他款项。一审法院经审理后认为:
美味不用等公司以客观情形发生重大变化为由解除与廖荠野的劳动合同但未提供证据予以证明,因此属于违法解除。但廖荠野属于外国人就业,按照相关规定,外国人在中国就业仅适用最低工资、工作时间、休息休假、劳动安全卫生等劳动标准,对于双方其他劳动权利义务可按双方合同约定予以确定。现双方签订的劳动合同中并未明确用人单位违法解除劳动合同时的民事责任,且廖荠野也未证明其遭受的损失,故廖荠野主张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的依据不足,美味不用等要求不支付赔偿金的请求予以支持。
一中院二审直接认定:
本院认同一审法院关于在双方无约定的情形下,廖荠野作为外国人不应直接适用我国劳动合同法关于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的法律规定的认定,廖荠野主张美味不用等公司应支付其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差额,缺乏法律依据。
(二)二中院:即便是到期终止但不续签仍要支付补偿金
在二中院终审的“(2016)沪02民终9210号”案件中,外籍员工Cornelia与上海德国学校签署一份终止日为2015年7月31日的《劳动合同》,上海德国学校于2015年4月14日发邮告知Cornelia合同到期后将不再续签。
合同到期终止后,Cornelia向劳动争议仲裁委申请仲裁,要求上海德国学校支付合同到期不续签的经济补偿金,仲裁委经审理后裁决支持Cornelia的请求。上海德国学校遂向青浦区人民法院起诉,请求法院判决不予支付经济补偿金。
一审法院审理后认为:
外国人在国内就业的,仅在最低工资标准、工作时间、休息休假、劳动安全卫生以及社会保险五个方面适用我国劳动基准法的规定,其余事项可按照双方约定或实际履行的内容予以确定。现Cornelia、上海德国学校之间签订的劳动合同于2015年7月31日到期终止,而双方未就终止劳动合同的经济补偿金作出约定,故Cornelia要求上海德国学校依据《劳动合同法》支付不续签劳动合同的经济补偿金的诉讼请求缺乏依据,不予支持。
上述判决表明一审法院的观点与一中院的终审观点相同。但Cornelia不服向上海市二中院提起上诉,二中院在审理后认为:
《劳动合同法》对于用人单位支付劳动者经济补偿金适用的情形有明确的规定。Cornelia与上海德国学校之间建立了合法的劳动合同关系,应受到《劳动合同法》的保护。鉴于双方在劳动合同中对合同期满终止劳动关系的法律后果未做明确的约定,因此双方应当按照《劳动合同法》的相关规定履行。据此,Cornelia要求上海德国学校支付经济补偿金的请求成立,应予支持。
二中院对一审法院判决予以改判,表明其认为《劳动合同法》中关于经济补偿金或赔偿金的规定对外国人同样适用。
3 结 语
从上述分析中可以看出,外国人的劳动纠纷如何适用法律问题的不同意见,根源在于《劳动合同法》和《外国人在中国就业管理规定》两部规定之间尚未完全调和。一方面来看,《劳动合同法》属于上位法,应当适用;但从另一方面来看,《管理规定》是特别法,在实践中应用性更强。正是存在进一步解释的空间,导致司法实践中存在类案不同判的现象,这一现象在上海市一中院和二中院这两个终审法院辖区体现的十分明显。
从上海市人社局在《劳动合同法》颁布后仍延续《关于贯彻<外国人在中国就业管理规定>的若干意见》的有效期这一行为,以及上海市高院在《劳动合同法》颁布前后对相关问题的规定来看,上海市人社局和上海市高院的态度更倾向于尊重用人单位和外籍员工之间的约定,除最低工资、工作时间、休息休假、劳动安全卫生等基本权利义务适用法律强制性规定外,其他权利义务可由双方在合同中自由约定。但是上海市二中院并未严格遵循上述意见,而是倾向于“内外一致”,赋予外国人“国民待遇”,对涉及外国人的劳动纠纷也严格依据《劳动合同法》来判定双方的权利义务。
我们认为,上海市人社局和上海高院的相关意见更具有合理性:
一方面,外国人就业问题本身已经被《管理规定》纳入一项行政许可,表明其与本国人就业是有所区别的,不能简单等同视之,这种特殊管理已经突破了《劳动合同法》的原则,所以对于涉及外国人的劳动纠纷也不能机械适用《劳动合同法》。
另一方面,赋予一些外国人“国民待遇”可以体现我国的包容性,但是对象一定要有所限制,不能任意扩大,尤其是作为社会法领域的劳动法关系到最广大人民的切身利益,在“如何正确雇佣外国人(一)”中我们已经表明本文所述“外国人”不包括已取得我国定居权的外国人,就是因为对于已取得定居权的外国人我国已经赋予其“国民待遇”,《外国人在中国永久居留享有相关待遇的办法》规定:“除政治权利和法律法规规定不可享有的特定权利和义务外,原则上和中国公民享有相同权利,承担相同义务。”对于这类外国人可以直接适用《劳动合同法》在法律规定和实践层面均有一致观点,但是将这种“国民待遇”推广到普通外国人身上并不合适。
再者,由于存在稀缺性,外国人在华工资待遇普遍较高,远超我国的社会平均工资水平,在这样的前提下如果对其严格适用《劳动合同法》中保护弱势劳动者的规定,其实际造成一种实质的不公平。
责任编辑:杜小娟